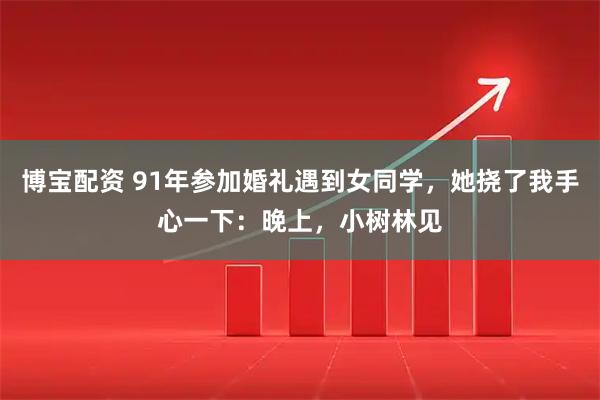
1991年的夏天博宝配资,蝉声嘶力竭地鼓噪着,搅得空气都带了粘稠的质感。我坐在人头攒动的婚宴席上,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硬的白衬衫领口,紧紧地箍着脖子,捂出了一层薄汗。桌上杯盘狼藉,弥漫着饭菜油脂和酒精混杂的气味,喧闹的人声像潮水一样一波波涌来,让我这习惯了与数字和账本打交道的脑子有些发懵。
我叫李向南,是个会计。此刻,我衬衫口袋里一如既往地别着两支钢笔,一支灌足蓝黑墨水,用来登记随礼的份子钱——这活儿刚才已经完成了;另一支是红色的,备用。它们像我的护身符,别在那里,心里才踏实。
同桌的都是些不太相熟的面孔,大约是新娘家那边的远亲或者邻居。我正盯着面前那杯浮着几片茶叶的茶水走神,盘算着什么时候离场比较不失礼,身旁的空椅子忽然被拉开了。
一阵淡淡的、像是栀子花的香气飘了过来,冲淡了周遭浑浊的空气。我下意识地侧过头,看见一个穿着淡紫色连衣裙的姑娘坐了下来。她侧对着我,正把一只黑色的、有些旧了的皮包放在膝上,一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子从肩头滑落,辫梢系着一根最普通的黄色橡皮筋。
我的心跳,毫无预兆地漏跳了一拍。
那辫子,那侧影,太过熟悉。即使过了这么多年……
展开剩余94%她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目光,转过头来。额前有些细碎的绒毛,被汗濡湿了,贴在光洁的额角。那双眼睛,还是像以前一样,亮晶晶的,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。她看见我,明显也愣了一下,随即嘴角弯了起来,露出那两个浅浅的、却仿佛盛满了夏日所有甜意的梨涡。
王春花。
是坐在我高中教室前三排的那个王春花。是那个每次回答问题时声音不大,却总能引得后排男生悄悄张望的王春花。是那个笑起来,能让窗外燥热的阳光都变得温柔几分的王春花。
时间仿佛在她身上停滞了,只是褪去了少女的青涩,增添了几分沉静和温婉。她比从前更好看了。
“李向南?”她先开了口,声音不高,带着点惊喜的笑意,“真巧啊,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。”
“啊……是,是巧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巴巴的,连忙端起面前的茶杯,想喝口水掩饰一下瞬间的局促。手指却不听使唤,微微发着抖,杯沿碰到牙齿,发出轻微的磕碰声。
“你也认识新郎还是新娘?”她笑着问,很自然地拿起桌上的茶壶,给自己也倒了一杯。
“新娘,是我远房表妹的同学。”我努力让呼吸平稳下来,“你呢?”
“新郎是我堂哥。”她抿了一口茶,目光在喧闹的人群中随意地扫过,然后又落回到我脸上,“好多年没见了,你现在在做什么?”
“会计,在县里的纺织厂。”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,这是紧张时不自觉的习惯动作,“整天跟数字打交道。”
“挺好的,安稳。”她点点头,眼神里没有一般人听到“会计”二字时常有的那种疏离或无趣,反而带着一种纯粹的、替人高兴的光芒,“你以前数学就特别好,看来是学以致用了。”
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聊这场婚礼,聊记忆中模糊的同学,聊这些年县城的变化。大多是她在问,我在答。她说话时,眼神总是很专注地看着我,让我有些不自在,又隐隐有些欢喜。周围的嘈杂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膜隔开了,我的世界里,好像只剩下她轻柔的嗓音和那双含着笑意的眼睛。
宴席接近尾声,有人开始离席走动、敬酒。场面更加混乱。她站起身,似乎要去洗手间。我也下意识地跟着站了起来,给她让出空间。
就在她侧身从我面前经过的那一刻,宽大的裙摆拂过我的裤腿。一只手,温软而带着微湿汗意的手,极快极轻地擦过了我垂在身侧的手心。
不是无意的碰撞。
那触感清晰无比——她的指尖,带着一种试探,一种小心翼翼的亲昵,在我掌心极其迅速地挠了一下。
像一片羽毛拂过,却带着电流。
“嗡”的一声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手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了一下,差点带翻了身后椅子靠背上挂着的、别人脱下的外套。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起来,震得耳膜都在嗡嗡作响。
我僵在原地,几乎无法思考。
而她,已经像一尾灵巧的鱼,混入了熙攘的人群缝隙中。只是在身影即将被完全淹没前,她极快地回了一下头,嘴唇微动,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气声,抛下了一句:
“晚上八点,村东头河边的白杨树林。”
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我怔怔地站在原地,手心里那一下微痒的、带着体温的触感,非但没有消失,反而像一颗投入静水的小石子,漾开一圈又一圈越来越大的涟漪,反复冲刷着我的神经。
王春花……她这是什么意思?
小树林?晚上?
无数个念头像沸腾的水泡一样冒出来,又噼啪碎裂。高中时那些几乎被我遗忘的细节,此刻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。她回头借橡皮时看过来的眼神;运动会上,她偷偷塞在我书包里的那瓶汽水;毕业那天,她好像在我课桌前停留了一会儿,欲言又止……
这些被漫长岁月和枯燥账本掩埋的琐碎片段,此刻都被手心那一下微痒的撩拨博宝配资,重新激活了。
去,还是不去?
这个问题像两个小人,在我脑子里打了一下午的架。理智告诉我,这太唐突,太不合规矩,我一个循规蹈矩的会计,怎么能深夜去小树林赴一个女同学的约?可另一种从未有过的、汹涌而陌生的情绪,却像野草般疯长,驱使着我,诱惑着我。
最终,那种混合着紧张、好奇、还有一丝隐秘期待的复杂情绪,战胜了平日的刻板。
我提前了整整半个小时出发。
夏夜的乡村小路,被月光照得朦朦胧胧。稻田里蛙声一片,和远处村落传来的几声狗吠交织在一起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、青草和晚香玉混合的浓郁气息。我走得很急,额上、背上又沁出了汗,手心也一直是湿漉漉的。
村东头的河边,果然有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。树叶在夜风里发出哗啦啦的响声,像是无数只手掌在轻轻拍打。林间光影斑驳,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,洒下零零碎碎的银辉。
我放轻脚步,拨开垂落的枝条,往里走了十几米。林中有一小片空地,月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,照亮了一个孤零零的树桩。
而那个树桩上,已经坐了一个人。
是王春花。
她果然来了,而且,来得比我还早。
她换下了白天那身淡紫色的连衣裙,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衬衫,下身是一条蓝色的及膝裙子。她就那样安静地坐在那里,双手抱膝,微微仰着头,看着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。侧影在清辉勾勒下,显得格外恬静,裙摆的边缘,真的被月光染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淡蓝色。
听到脚步声,她转过头来。看到是我,她脸上立刻绽开了一个笑容,比白天的笑容更明亮,更毫无保留。她晃了晃手里不知什么时候摘的一捧野雏菊,白色的花瓣在月光下微微发着光。
“李向南,”她的声音带着笑意,清晰地传来,“你知不知道,我等这天,等了七年了?”
七年?从我们高中毕业算起,正好七年。
我愣在原地,推了推眼镜,喉咙有些发紧。七年……她等这天,等了七年?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,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我张了张嘴,想说点什么,比如“我没想到”,或者“为什么是我”,又或者,只是叫一声她的名字,“春花”。
可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,没能发出一个清晰的音节。
就在这短暂的僵持间,她忽然从树桩上跳了下来,几步走到我面前。那股淡淡的栀子花香,再次将我笼罩。她仰着脸看我,眼睛亮得惊人,里面跳动着狡黠而勇敢的光。
然后,她伸出手,目标明确地探向我衬衫左上方的口袋。
我完全没能反应过来。
只觉得胸口被极轻地触碰了一下,那支灌满了蓝黑墨水、我最常用的钢笔,就已经被她抽了出去,握在了她那白皙的手里。
冰凉的金属笔夹擦过布料,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
她将钢笔举到我们两人之间,像是举着什么战利品,嘴角扬起一个得意又带着点俏皮的弧度。
“现在,”她晃了晃那支钢笔,眼睛弯成了好看的月牙,“你跑不掉了,会计同志。”
我怔怔地看着她,看着那支在她指间显得格外熟悉的钢笔,再看看她脸上那混合着羞涩、勇敢和无比确定的笑容。那一刻,所有盘旋在脑海里的疑问、顾虑、紧张,仿佛都被一阵清风吹散了。
一股温热而澎湃的暖流,从心口汹涌而出,瞬间流遍了四肢百骸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,夏夜清凉而芬芳的空气涌入肺腑。脸上不由自主地,也露出了一个笑容。大概有点傻气,但却是发自内心的。
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,轻声说,语气里带着连我自己都惊讶的镇定和温柔:
“嗯,不跑了。”
那句话像有魔力,瞬间打破了我们之间那层看不见的薄冰,也融化了我心底最后一丝犹豫和拘谨。空气里那点微妙的紧张感,被她这句带着娇嗔又霸道的“会计同志”给冲得烟消云散。
我看着她紧紧攥着我的钢笔,仿佛真的怕我转身跑掉的样子,心头软得一塌糊涂。月光下,她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,眼神亮得惊人,勇敢背后,还是泄露了一丝属于姑娘家的羞怯。
“钢笔你拿走,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笑意,出奇地平稳,“我的账本可都在厂里,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
她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,眉眼弯弯,那对梨涡更深了,盛满了蜜糖般的月光。她把手背到身后,依旧握着那支钢笔,仿佛那是她最重要的筹码。“那也不行,得押在我这儿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赖账。”
那晚,我们在那片被月光笼罩的白杨树林里待了很久。就坐在那个粗糙的树桩上,肩并着肩博宝配资,距离近得我能闻到她发间淡淡的皂角清香,能感受到她身上传来的、属于夏夜的温热气息。
我们说了很多话,比高中三年加起来说的还要多。大部分时间是她说,我听。她说起高中毕业后没能继续读书的遗憾,说起她在镇小学做代课老师的琐碎与快乐,孩子们如何调皮,又如何用稚嫩的画作让她感动。她说起家里的情况,父母的期望,还有那些不痛不痒、却被家人催促着相看的亲事。
她的声音不高,带着点柔软的乡音,像清凉的溪水流过心田。我安静地听着,偶尔插一两句话。我告诉她我这七年如何与数字为伍,如何在算盘珠子的噼啪声和账本的表格格里,度过一个个白天和夜晚。我说起厂里那些老师傅的趣事,说起核对账目时发现一分钱差额时的焦头烂额。
这些平淡无奇、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,在此刻说来,却仿佛都镀上了一层别样的光晕。因为她在听,很认真地听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,仿佛我说的不是琐碎的会计工作,而是什么了不得的冒险故事。
“其实……高中那会儿,”她忽然低下头,声音更轻了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树桩上的裂纹,“我就觉得你跟别的男生不一样。你安静,不爱闹,但每次看你解数学题的时候,眉头微微皱着,特别……嗯,特别认真。”
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原来,在我偷偷注意着她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时,她也曾留意过我这个坐在后排、默默无闻的男生。
“我记得,”我接过话头,勇气也莫名地增长了几分,“毕业那天,你在我桌子旁边站了一会儿,我以为你有什么事。”
她猛地抬起头,脸颊更红了,眼神里带着被戳破心事的慌乱,随即又化作一种释然和娇嗔:“你看到了?我……我当时鼓了好大的勇气,想跟你说句话,可你一直低着头整理书包,我……我就没敢。”
月光静静地流淌,在我们之间织成一张温柔无声的网。林中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还有彼此清晰可闻的呼吸声。一种无需言说的情愫在静谧中疯狂滋长,饱满得几乎要溢出来。
“春花,”我唤了她的名字,感觉这两个字在舌尖滚过,带着前所未有的亲昵和郑重,“那瓶汽水……运动会上,是你放的吧?”
她抿着嘴笑,轻轻点了点头。
“为什么……是我?”我终于问出了这个盘旋在心头一下午,不,是盘旋了七年的问题。
她沉默了片刻,然后抬起头,目光清澈而坚定地看着我:“我也不知道。可能就是觉得,你踏实,可靠,像……像一棵树,安静地长在那里,让人看着就心里安稳。”她顿了顿,声音更柔了,“而且,你笑起来……其实很好看,只是你以前都不怎么笑。”
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彻底击中。从未想过,在我按部就班、近乎刻板的生活里,会有人这样注视过我,珍藏了这些我自己都未曾在意过的细节。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月亮渐渐西斜。林间的光线愈发朦胧,露水也重了起来。
“不早了,”我虽然万分不舍,还是不得不提醒她,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她乖巧地点点头,站起身,拍了拍裙子上的碎屑。
回去的路,我们走得很慢。乡间小路静谧无人,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和虫鸣。我们的肩膀偶尔会碰到一起,又迅速分开,那短暂的接触像火星溅落,烫得人心尖发颤。有好几次,我的手背擦过她的手背,肌肤相触,带来一阵微麻的战栗。
快到她们村口的时候,我停住了脚步。“就送到这儿吧,再近怕被人看见,对你不好。”
她“嗯”了一声,站定,抬头看我,眼神里满是不舍。她终于把一直攥在手里的钢笔递还给我:“喏,还给你。”
我接过钢笔,金属的笔身还带着她的体温和汗意。我没有把它放回口袋,而是紧紧握在手心,仿佛握住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。
“明天……”我几乎是脱口而出,“明天厂里休息,我……我来镇上找你?听说镇上新开了家面馆,味道不错。”
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,像落入了星辰。“好呀!”她应得飞快,带着掩饰不住的欢喜。
看着她转身,小跑着消失在村口的阴影里,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胸腔里被一种前所未有的、饱满而滚烫的情绪填得满满的。握着那支带有她体温的钢笔,我独自走在回返的路上,夏夜的风拂面,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舒畅。天上的星星仿佛都比来时更亮了些。
从那一天起,我那原本只有数字、账本和条条框框的世界,被一道名为“王春花”的阳光,毫无预兆地照了进来。
我们开始了频繁的见面。大多数时候,是我下班后,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,叮叮当当地穿过夕阳,去镇小学门口等她。她总是最后一个出来,收拾得清清爽爽,看到我时,脸上会立刻绽放出那个专属于我的、带着梨涡的笑容。
我们一起去吃镇上的那家面馆,她总是习惯性地把她碗里的煎蛋夹给我,说我工作费脑子,要多吃点。我们一起在傍晚的田埂上散步,说些没什么营养却乐在其中的闲话。她跟我分享班上孩子的趣事,我则跟她抱怨某个账目总是对不平的烦恼。她有时会调皮地考我数学题,都是些小学生的题目,我却每次都装作苦思冥想,逗得她咯咯直笑。
我也会带她去县里。看一场电影,散场后在灯光昏暗的街道上,手指小心翼翼地勾住她的,她挣一下,没挣开,便红着脸任由我牵着。去新华书店,我帮她挑教学用的参考书,她则对那些封面漂亮的诗集流露出喜爱,我默默记下,下次便买来送她。她收到时,眼里闪动的光彩,比任何数字都让我心动。
感情像春日的藤蔓,悄无声息地疯长,缠绕得紧密而牢固。我变得越来越不像原来的那个李向南。口袋里依旧别着两支钢笔,但心里却装进了一个鲜活、生动、会笑会闹的王春花。我会因为她一句“会计同志今天表现不错”而偷偷开心一整天,也会因为她偶尔提起某个男老师对她似乎有些关照而暗自酸涩半天。
见过几次面后,我决定带她回家见我父母。
去之前,我有些忐忑。我家就是普通的工人家庭,父母都是老实本分人,而春花家里是镇上的,父亲是小学副校长,母亲在供销社工作,条件比我家要好些。我怕他们觉得我家境普通,配不上春花。
那天,春花特意穿了一件素净的格子连衣裙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给我父母带了精心准备的礼物——给我父亲的两瓶好酒,给我母亲的一块柔软的羊毛围巾。她落落大方,说话得体,吃饭时主动帮忙收拾碗筷,和我母亲聊家常也丝毫不怯场。
饭后,母亲私下拉着我,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:“向南,春花是个好姑娘,模样好,性子也好,一点不娇气。你可要好好对人家。”
父亲话不多,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,眼神里是赞许和放心。
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然而,事情到了春花家那边,却遇到了一些阻力。
正如我预料的,春花的父母,尤其是她父亲,对女儿找一个“县纺织厂的小会计”颇有些微词。倒不是嫌弃我这个人,主要是觉得会计工作没什么大出息,收入也有限,怕女儿跟着我吃苦。
我第一次正式登门,气氛就有些微妙的凝滞。王校长戴着眼镜,坐在藤椅上,慢条斯理地喝着茶,问了我的工作、家庭情况后,便陷入了沉默,只是偶尔抬眼打量我,目光锐利。春花的母亲倒是客气,张罗了一桌好菜,但笑容里也带着几分审视。
那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,手心一直在冒汗。春花在桌下悄悄踢我的脚,给我递来鼓励的眼神。
饭后,王校长终于开了口,语气严肃:“小李啊,你和春花的事,我们做父母的,原则上不反对。年轻人自由恋爱,是好事。但是,”他话锋一转,“生活是现实的。你就打算在纺织厂当一辈子会计吗?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发展?比如,考个职称?或者,有没有别的打算?”
我深吸一口气,放下一直端着的茶杯,坐直了身体。来之前,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关。 “伯父,伯母,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,“我知道,会计这份工作,在很多人看来,确实平淡,甚至有些枯燥。
收入也不算很高。但我热爱这份工作,数字和账本在我眼里不是冷冰冰的,它们关系到厂里几百号人的生计,把它们理清楚,保证分毫不差,我觉得很有意义,也很有成就感。”
我看到王校长的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 我继续诚恳地说:“关于未来,我有规划。我正在准备参加今年的会计员资格考试,如果能通过,工资和岗位都能提升一步。而且,厂里的老会计年底就要退休了,领导之前暗示过,有意让我接他的班。
我不敢说能大富大贵,但我可以向您二位保证,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,让春花过上安稳、舒心的日子。我不会让她受委屈,更不会让她为生计发愁。” 我一口气说完,心跳如鼓,但目光没有躲闪,坦然地迎接着王校长的审视。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。
忽然,王校长端起茶杯,又喝了一口,然后轻轻放下。“嗯,有想法,有规划,不错。”他脸上的线条似乎柔和了一些,转向春花母亲,“去把我那盒新茶叶拿来,给小李尝尝。” 我提到嗓子眼的心,猛地落回了实处。
我知道,这第一关,我算是勉强通过了。 接下来的日子,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复习中。春花成了我最得力的“后勤部长”和“监督员”。她帮我找复习资料,在我熬夜时给我煮鸡蛋、泡浓茶,在我偶尔懈怠时,会拿出那支钢笔在我面前晃一晃:“会计同志,思想可不能开小差哦。” 她的支持,成了我最大的动力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那年秋天,我顺利通过了会计员资格考试。成绩出来的那天,我第一个跑去告诉她。她高兴得像个小孩子,在原地跳了起来,然后不顾周围还有人,紧紧抱住了我的胳膊。 这个消息,无疑也传到了王校长耳朵里。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,但再次见到我时,脸上的笑容明显真诚了许多,甚至开始会跟我聊一些时事和教育工作了。
我知道,我们之间的障碍,正在被一点点清除。 又是一个夏夜,距离我们在白杨树林初次约会整整一年。我约她再次去了那里。 月光依旧,白杨树林哗哗作响,那个树桩也还在老地方。 我们像去年一样,并肩坐在树桩上。不同的是,这一次,我的手自然而然地环住了她的肩膀,她也顺势靠在我怀里,气息交融,亲密无间。 “春花,”我低声唤她,感觉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,“有样东西给你。”
我从裤子口袋里,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红色绒布的小盒子。 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,身体微微僵了一下,抬起头,眼睛在月光下睁得大大的,里面充满了惊讶、期待,还有一丝不敢置信。 我打开盒子,里面是一枚金戒指,样式很简单,却闪着温润的光。
这是我用几乎所有的积蓄,加上考试通过后厂里发的一笔奖金,托人在市里的金店买的。 “春花,”我看着她,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,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无比清晰、郑重,“嫁给我,好吗?我不敢说能给你世上最好的生活,但我保证,我会用我往后余生的所有时间,对你好,让你幸福。我的账本、我的钢笔、我这个人,以后都归你管。”
她没有立刻回答,眼睛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光,亮晶晶的,比天上的星星还璀璨。她看着我,看了很久,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,眼泪终于滚落下来,却带着灿烂无比的笑容。 “好。”她带着哭音,却无比坚定地说,“我管你一辈子,会计同志。”
她伸出手,我颤抖着,将那枚小小的戒指,套在了她左手的无名指上。尺寸刚刚好。 她举起手,对着月光仔细地看着,然后又哭又笑地扑进我怀里,紧紧抱住了我。 那一刻,白杨树林的喧哗,夏夜的虫鸣,仿佛都成了为我们奏响的祝福乐章。
我拥抱着怀里的姑娘,感觉拥抱住了我整个世界的圆满。 提亲、订婚,一切都水到渠成。王校长终于彻底放下了那点最后的顾虑,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婚事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向南,把春花交给你,我放心了。” 1992年的春天,桃花盛开的时候,我和王春花结婚了。
婚礼不算特别盛大,但很温馨。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,胸口别着那支意义非凡的钢笔。当她穿着红色的嫁衣,蒙着红盖头,被她父亲牵着交到我手上时,我的手心依旧像一年前那个晚上一样,因为紧张和激动而满是汗水。
我紧紧握住她的手,这一次,再也没有松开。 闹洞房的人散去后,新房里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红烛高燃,映得满室温馨。 她坐在炕沿上,低着头,脸颊绯红,比任何時候都要娇美。 我走过去,在她身边坐下,从口袋里再次掏出那支钢笔。
她看到钢笔,忍不住笑了:“怎么还带着它?” “当然要带着,”我把钢笔放在她手里,连同我的手一起握住,“这是定情信物,得保管好。” 她靠进我怀里,轻声说:“李向南,我现在真的把你‘抓’住了。”
我低头,吻了吻她的发顶,心中被巨大的幸福和满足填满。“嗯,抓得牢牢的,一辈子都跑不了。” 婚后的生活,平淡,却蜜里调油。 我依旧在纺织厂做我的会计,她还在镇小学教书。
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不大的宿舍里,她把那里布置得温馨而整洁。每天清晨,我们一同在公共水池边洗漱,然后我骑车送她去学校,再去厂里上班。傍晚,我再去接她下班,一起买菜,回家做饭。
她做饭的手艺很好,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美味的菜肴。我们围着小小的折叠桌吃饭,说说各自单位里的趣事,计划着周末去看望父母,或者存钱买一台她想要的洗衣机。 晚上,我在灯下核对账目,她就在一旁批改学生的作业,或者备课。
台灯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俩,房间里只有纸页翻动和笔尖划过的沙沙声。偶尔抬头,目光相遇,相视一笑,便觉得岁月静好,莫过于此。 那支钢笔,依旧别在我的口袋里,只是旁边,多了一支她给我买的、据说更好用的新钢笔。但她送的那支,我始终舍不得换掉。
一年后,我们的女儿出生了。给她取名字的时候,春花说:“你姓李,我姓王,咱们女儿,就叫李望吧,希望的望。” 小名望望。 望望的到来,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忙碌和琐碎,也带来了数不尽的欢笑。我学着给她换尿布,笨手笨脚地哄她睡觉。春花则变得更加温柔而有力量,一边照顾孩子,一边依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又是一个夏夜,望望已经睡着了,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我们轻手轻脚地收拾好一切,并肩坐在窗边的小床上乘凉。月光如水银般泻入室内,在地上投下清晰的窗格影子。 春花靠在我肩上,看着窗外的月亮,忽然轻声说:“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,望望都会叫妈妈了。”
我揽着她的肩膀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她睡衣的布料。“是啊,感觉昨天还在白杨树林里,你挠我手心呢。” 她吃吃地笑了起来,抬起头,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:“后悔了?” 我低下头,准确地找到她的嘴唇,印下一个温柔而绵长的吻。
“后悔,”我在她唇边低声说,“后悔没让你早点挠。” 她笑着捶了我一下,然后把头更深地埋进我怀里。 窗外,蝉声依旧,月光温柔地笼罩着这片承载了我们开始的土地。
从1991年夏天那个令人心慌意乱的挠手心开始,到如今怀中真实的温软,这条叫做“幸福”的路,我们走得踏实而满足。 我知道,未来或许还会有风雨,有坎坷,但只要我口袋里的钢笔还在,只要我身边这个叫王春花的女人还在,我的世界,就永远晴朗,永远账目清晰博宝配资,爱意分明。 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
发布于:陕西省融胜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